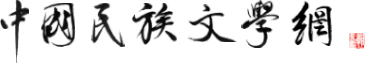霍达这个名字近年来很少见诸媒体,但她的代表作《穆斯林的葬礼》却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冰心老人在1990年为这本书的外文版作序称之为“一本奇书”。霍达自己都记不清这本书自1988年出版至今已印刷了多少次出版了几百万册了。而两部新长篇正在她手中同时挥洒,分别名为《悟》和《天涯倦客》。
这两天,又有上万册《穆斯林的葬礼》散发着墨香走上各书店书架,只消三两个月,它们便会被销售一空。据出版该书的北京十月出版社称,抛开以往的不算,这次是他们自1998年对该书改版以来第21次重印了。
1写作之痛——我以为自己的葬礼要先举行了
记者:您1987年写完了《穆斯林的葬礼》,与那个年代其它一些作品相比,这部书十几年来一直长销不衰,您觉得是为什么?
霍达:两个字:幸运。如果非要说理由,我认为可能是我的真诚,我写作从来不太考虑社会效应如何,我只想首先感动我自己,再感动别人。一个怀有真善美之心的人才可能写出好的文章,否则再有才华,从道德品质上讲是个卑劣小人,那他绝不会有真正的创作成就。
记者:我听说当时的写作过程非常痛苦,您心绞痛反复发作,边写边吞药才完成,现在写作还是这样吗?
霍达:写这本50万字的书,你知道我用了多长时间?四个半月!可前期准备工作时间相当漫长,可以说是从我懂事起,就酝酿着想写这本书。提笔前我踏着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足迹四处奔走,看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历史就像在我的面前复活了。我在稿纸前常常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窗外正是三伏盛夏,书中却是数九严冬,我不寒而栗……我为书中主人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痛哭一场。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心绞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吞药。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葬礼先于书中的葬礼而举行……写作让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怕死,因为我早就死过好多次了。
现在写作我仍然这么投入,我不能像别的作家一样,写完一段,站起来对别人说,好了,我们先吃饭吧,我根本从书中出不来。写作的痛苦如蚯蚓爬过沙滩一样,留下的痕迹只有自己看得见。
记者:您写作是用笔还是用计算机?
霍达:以前写东西我都用计算机,因为影响写作思路,我又回到用笔写了,你看,手指都写僵了。有一次我去卫生站做理疗,碰上丁宁他们,没人敢认我了,满脸满身疲惫不堪。其实我大可不必这么辛苦,两个孩子都大了,王先生(她故意随我们称呼他)的画非常好卖。
2写作之乐—— 岁数最大的读者93岁
记者:写完后用什么方式调整自己了?知道发表后这么引起轰动吗?
霍达:没有喘一口气,马上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我知道有许多人喜欢这本书,我非常感谢这些读者。甚至有两位读者已经到了“强迫性思维”的地步,他们一男一女,三十来岁,一个是西安人,一个是河北人,除了每天给我打两三个长途电话外,还千方百计找到了我家,要帮我按摩、没完没了地想同我聊天,他们对《穆斯林的葬礼》《补天裂》中许多片断都倒背如流,我都不太敢接他们的电话了……
还有一位东北的书商,有一次与我谈另一本书的合作,他不小心透露说他靠《穆斯林的葬礼》赚了200万元。
记者:我周围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从20岁到60岁不等,且翻译成多国文字后在异域也同样为人所喜爱,对于书中描述的苦难与人性,您觉得下一代人还能理解吗?
霍达:你当时看的时候也就二十来岁,你觉得看懂了吗?我相信能理解,就像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你对他微笑,他能用同样的目光来响应你。人性是相近的,它不分年龄和国界。我知道的岁数最大的一位读者是93岁的老人,他对我说,“书中的韩子奇有原型吗?你能那么理解一个老人的心意,我走了也知足了。”他那句话分量真重!知道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的文字,无论多累,我都没法放下手中的笔。
3写作之情——担心飞机失事 把珍贵资料寄一份给丈夫
记者:最近在做什么创作?
霍达:正在写两个长篇,一本写女性的叫《悟》,一本反映海峡两岸几个家庭悲欢离合的叫《天涯倦客》。我写作一般都是先定好书名才开始动笔。很少在成书后再改动,当年《穆斯林的葬礼》也是,动笔前三年我就想好了书名。
记者:您除了《穆斯林的葬礼》,还有《补天裂》《红尘》《年轮》等多部小说和报告文学,但最有影响的还是《穆斯林的葬礼》,您眼中的这本书是否与众不同?
霍达:说实话,我最得意的还不是这本书,而是《补天裂》,有评论称“那是部史诗”。
在我以往的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晚清史却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因为那是一段充满民族屈辱的历史。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萌生了以小说形式再现香港历史的念头,经过陆续几年的准备,1994年我终于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开始了历时三年的采访和调查研究。之前不久,有位富翁出500万港元要我为他写自传,我拒绝了。
记者:讲讲在香港搜集素材时的事情吧。
霍达:说这些好像有自夸的嫌疑。当时在图书馆翻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数千万字,看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会兴奋得发抖,赶紧复印四份,其中一份寄给远在北京的丈夫,由他保留着,为什么?我怕万一飞机失事我死了不就白找了吗?
我还实地踏勘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探寻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往往是每天早上八点半起来,带着地图或坐公交车或步行,走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荒山野岭。当时每天早出晚归,往往回到住处后整理数据到半夜,把电视调到央视4台,不管里面说什么呢,我都会感觉自己离家那么近。
4生活之爱—— 我最不能舍弃的是我先生
记者:如果这世间让您对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进行选择,您最不能舍弃的是什么?
霍达:(毫不犹豫)我最不能舍弃他——我的先生。
记者:《穆斯林的葬礼》中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让人神往,您怎么看待爱情?
霍达:爱情不是口头上的东西,在我现在看来,青年人的爱往往是性爱,中年人是情爱,到了晚年才是爱情。相爱的人应该以命相许、以命相托。在我的生命中我无法想象没有我先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探讨过,如果不能一起走,我希望我先离开世界,由他来料理后事;如果他先走了,我很快会随他而去,因为没有他,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5生活之重——文学是母亲,话剧是爱人,电影是情人
记者:您曾说过写作是为书中人物的心灵作传,一向都是比较纯凈严肃、甚至是有使命感的写作,如今人们对待写作的态度越来越宽松,您怎么看?
霍达:我感觉很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写作的态度越来越慎重。在我眼里,文学对一个民族来讲是母亲,话剧是爱人,电影是情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学不可以太不严肃,它代表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境界。像戏说历史呀,美女作家的私人写作呀,我认为无可指责,但我自己是不会去看的。一些浅薄的“现代文化”将人们丰富细腻的情感一带而过,致使社会上许多人随便地同居、闪电般结婚、轻易地分手……越是这样,人们越向往宝黛的纯情,向往韩新月与楚雁潮的完美。这也是好多作品畅销的理由,没什么便盼什么呀。
6生活之思—— 我现在是个“堕落”的人
记者:您怎么评价自己的现在?
霍达: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堕落”的人。以前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时,为了将一个受害人的真相公之于众,我能一口气奔走于37个县,顶着巨大的压力到村子里面找农民谈话,真是为民请命啊。哀莫大于心不死,我非常关心国家命运,老想把作家与政治家合一,我真心希望我们的民族越来越富强。
怎么看待宗教?
霍达:我认为应该把宗教当成一种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是奉献,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只拘泥于形式。(记者李冰/文张珂/摄)
□采访手记
是她,当年让我痛哭
早在八年前,在一个秋天的黄昏,我一个人伏在家里那张旧沙发上痛哭失声,泪水打湿了衣裙、椅垫,直到父母回家见了吃惊地询问理由。当他们看到茶几上那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时,父亲立即平静了,他说:她一定是看到新月死了。那本有着素凈封皮的书是他一个月前买回家的,只三天,他便读完了,却很久一言未发,第二天是他把书放到了我的书桌上。
八年后的这个周五,天是阴的,在和蔼的丁宁大姐的引领下,我与霍达挨肩坐在了她家的沙发上,丁宁是出版社编辑,近几年霍达几乎所有作品的责编。“《穆斯林的葬礼》据我所知已经重印了三十多次,长销不衰,我们今年又加印了三万本。至于怎么形容她,你还是等会儿自己来判断好了,我不想影响你……”在路上,善解人意的丁宁似乎有意要替霍达保留最后一份神秘。
我们的采访地点定在画家王为政--霍达丈夫的书房。整洁、宽敞的房间,光线有些暗。很明显,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墙上挂着几张二人站在街头相依的大幅合影,靠门的一张画像上则是一位文雅端正的年轻女孩,有些褪色的字迹是“1971年1月4日”,那是画家在新婚第三天为爱妻所作的。
“给客人沏茶了吗?刚才不是已经泡好茉莉了吗?来,喝吧,这些茶具都是消过毒的。”卷发,微胖,明亮的眼,爽朗的笑,我不知道是否眼前的霍达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人,那个让我在青春期头一次不是为了自己的爱情而泪流满面的女人,想象中,躲在书后的她应是瘦高且冷傲的,像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看我们打量墙上的图片,她像个恋爱中的女人一样毫不掩饰地开玩笑说“是我追得他,你们看见墙上那张自画像了吗?是他四十岁生日时在国外画的,我老公还挺帅吧?”那自豪与快乐是透明且温暖的,屋子一下亮堂了起来。
《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上世纪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最初1987年冬至1988年春发表于《长篇小说》季刊总第17、18期1987年第6期《中国作家》选载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评论为“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部成功表现了回族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1989年和199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节目两度全文播出本书1991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陆续出版了英、法、阿拉伯等文字的译本1992年,台湾《世界论坛报》以长达一年的时间全文连载本书。
我愿承受失去爱人的痛苦 霍达丈夫:我愿让她先走
我的意见对她不重要
随我们一起欣赏着墙上一幅幅画作,说起圈中的好友,画家王为政先生告诉记者:“我突然发现我与霍达圈中的友人多是岁数比较大的人,比如黄苗子啊,当年的吴祖光啊。我们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社交活动,尤其是艺术创作,那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说到将于本月25日迎来百岁生日的巴金,王先生说这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其中的50位名家作品中就有他作的一幅巴金画像。
趁霍达还没从楼上下来,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的王先生故意不动声色道:“趁她不在我赶紧瞎说会儿。”“霍达的作品您都看吗?”我问。“看,几乎出版前都看过。”他答。“提意见吗?”“也提,但好像不太重要。我不太赞成在学问上集体讨论。”即使说笑话,他脸上也看不见笑容,那满含爱意的笑火花般漾在眼睛里。他说他与霍达刚相识时并未觉得会走到一起,只是很相投的好友,渐渐彼此的信任与关怀让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像兄妹,再后来才发展为恋人。
“她的作品别人爱看,您觉得是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她是真诚地创作,奉献给读者的是自己的心血;第二她的所有作品都宏观、历史地聚焦某个题材,哪怕写《红尘》中拉三轮的小人物,也站在一定的高度。我认为作品可以有毛病,但不能没特色。”瘦而高的王先生看起来有些不拘言笑,但每说一句话都严谨而不乏幽默。采访中霍达回答某个问题不够及时,他便会接过话题来说两句。其间不管谁插进话来,他都非常有礼貌地停下来目光专注地看着讲话人,等大家都安静了才接着讲下去。与其说他是个画家,更不如说是个学者。
我愿承受失去爱人的痛苦
记者:《穆斯林的葬礼》、《红尘》等写的事都发生在北京,您认为霍达的写作算京味儿文学吗?
王为政:写京味儿小说不是口音上有几个“儿”化,要像老舍那样大雅若俗,一定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看世间的一切。即使写小市民也不是说要站在市民的水准在线,同他们一样思维。我不认为非要把她的作品归入哪一类,也不敢将她同老舍比,至于算不算京味儿我们好像也没考虑过。
记者:你们二位一个为文一个作画,两种不同的创作形式会对彼此产生什么影响吗?
王为政:这两者其实离得挺近的,我们经常会互相探讨,但都尊重对方自己的选择。
记者:霍达说您是她的“第一读者兼参谋长”,除了业务上的沟通,生活中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王为政:我和她都喜欢听诗朗诵,看好电影,读好书,当然旅游是我们最不可缺少的项目,每年都要出去好几次。她尤其喜欢自己朗诵,有时跟着人家电视或CD上忘情地念“何事长向别时圆”,我就会给她泼冷水说“我想听人家的行吗?”
离创作更近的爱好就是聊天,我们两人喜欢聊天,虽然有各自的卧室,好多时候她躺在床上,我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我们常常一聊就到凌晨了。
最讨厌的事情是打麻将牌,我们不理解那么单调枯燥的游戏为什么能让人一玩就是通宵。有一阵她母亲说教我们打麻将,结果一学都大叫没意思,从此再也不上牌桌了。
记者:霍达说她如果失去了您就会失去生命的意义,她执意要在您离世之前先离开人世,您同意吗?
王为政:(微笑着点头)我同意。我们商量好了,由我来料理后事。虽然人都不希望死,都有生的愿望,可我还是希望走在她后面,这样我就能承担最后的痛苦。
记者:霍达说都已设计好了离去时的场景:放着梁祝的音乐,床上铺上马蹄莲,在身上洒一些圣罗兰的香水,回忆过去的温馨片断,让最亲近的人最后看她两眼……您怎么看?
王为政:我能理解她。作为爱人我会支持她的一切。
□霍达小传
1945年出生,北京人,回族。毕业于某工科院校英语专业,曾在文物局从事文物工作,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上世纪70年代发表第一部小说《不要忘记她》。
霍达是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因文学创作的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种津贴。着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500万字,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小巷匹夫》获火凤凰报告文学奖。作品有英、法、阿拉伯等多种文字译本及港、台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