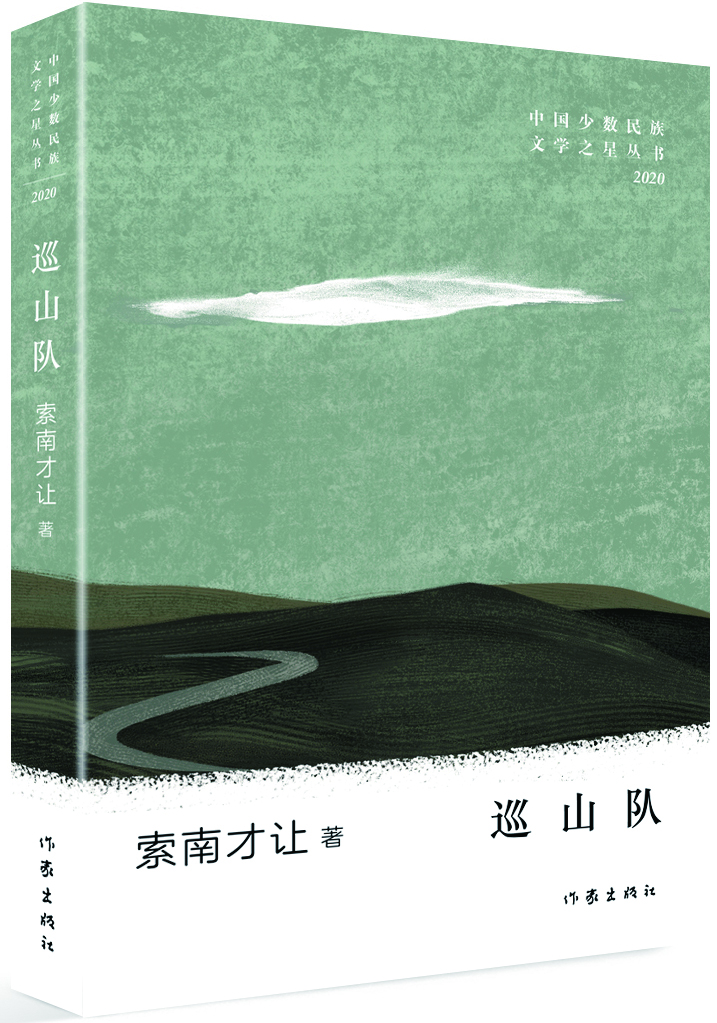
我第一次读让我迷醉的文学作品是在辍学之后,那应该是我14或者15岁。我在叔叔家里看到一本没有封面没有开头的书,我拿起来,随意地读了一段,就觉得很有意思。武功、侠客、江湖,这些东西正是我那个年龄段最需要的。我拿着那本书去放羊,那是冬天,黄沙漫天的日子,我一整天都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不知道时间,不知道羊群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是我真正意义上阅读的开始,如果没有阅读的开始就不会有后来的写作的开始。所以我的写作是从那次阅读开始的。
之后的10年,我越来越贪婪地阅读,不放过看到的每一本书。那真是一段黄金时期。到了二十几岁,突然有一天坐下来,写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叫《沉溺》。
我觉得在我想要写作之前,我的潜意识已经有了准备,然后传递给了身体,是我的身体第一个做出反应,我的手指已经在蠢蠢欲动,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写了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事实就是那样。我会主动幻想,对我而言是特别重要的前期准备。准备的过程中自然会有别的东西加进来,所以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小说的准备”是完成了的。它可能就是一点模糊的稍纵即逝的“片段”,但那也是我的精心准备。没有这个“片段”我基本上是下不了笔的。因为我缺乏了写作中最必要的东西。这种高度的模糊性是很多人所排斥的,但我想作家不应该在其中。作家的不确定、神经、多疑就是他的本质。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但不会全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创作。不管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我觉得首要问题就是语言。读者如果对你的作品第一页都读不下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你的语言不行。再好的故事都要有包装,语言就是包装。好的语言怎么来?当然需要锤炼,这就是技巧了。短篇小说的技术问题是硬件,得训练,但不要妄想技术有一天会至臻完美。我不相信有技术完美。所以我会尽力写出最好的状态,我更注重小说中的灵动性,这个不好说,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但一个小说如果写得太完满,读者就会感到遗憾,因为没有他要插足的余地。读者也是作者,他在阅读当中会对你的小说进行再创作,这样才有意思。
写作在我看来首先应该得有一种直觉,一种对笔下世界的直觉。这就像在找某件东西,突然强烈地感觉到它就在那个地方,虽然看不见但无疑就在那儿……
写作也有毒瘾。很多人不知不觉间被毒坏了。但强大的作家懂得斩杀过多的文学情怀,使之稳定在恰当的段位。文学是责任的、多情的。掀开一页纸,眼睛盯着写下的文字,所产生的影响谁也不知,自己也不知。但确实存在,哪怕一人也足够了。心灵的感应遥遥锁住某个裂变的地方……所以一旦写作,无法停止的不是手和心,而是强大的意志。
在写小说最初的几年,每到秋天,草原的颜色变幻之际,我都会住在青海湖边。我扎着帐篷住在青海湖北岸的尕海之畔,面朝大湖。火车一辆辆从后面的原野上掠过,永不停息。我就在这隆隆的滚动声和被风推动的浪花声中一边牧羊,一边写作。我在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费力地写着。黄昏的时候抽着烟,到很远的泉眼去提水。那里好几天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只孤独的黑颈鹤陪着我。大湖上吹来的风吹皱岸边的浪花,吹出一片天空的海的气息,吹动吃盐水的羊的脊背,吹响连成阵势的铁链的声音。
于是,这时候,整个大湖属于我!
而其他的时候,我依然有一半时间在帐篷里写作。那是在夏季牧场,营盘上的地皮因为羊群粪便的烧蚀和暴雨的冲刷而逐年脆弱,终于不堪使用了。那是我们家族祖祖辈辈使用的营地,如今即将寿终正寝。
我就在周围充斥着羊粪味的营地上,坐在小矮凳上伏在床上,用铅笔和笔记本,用三个夏季写了这部集子里的一些篇什。我写草原、牧场和牧人,写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写不得志的酒鬼,写转场途中的商店,写盗猎者、写屠宰者、写兽医、骏马、私生子,写鬼鬼祟祟的心思和带刺的感情……
我的作品几乎没有离开过草原。过去、现在是如此,估计将来也会是这样,这个谁知道呢?
后来我好几年没有去夏牧场,没有将身心放置于暴雨肆虐银电如鞭挥舞的夏夜,它让我失去了对天气和畜群的担忧。这是牧人不能缺失的警觉,而我正在远离。于是,我怀揣着牧人一生的主题——寻找,一个人开放了自己,飞向莽莽群山。晚上也住在山里,吃最简单的食物,睡祖辈传下来的被穴。听到了很多狼的嚎叫。那是我以前不怎么留意的声音,因为从小到大,听到的太多了。那些晚上,我躺在草地上,瞪着夜空,我回忆这些年的生活。世事无常,我何以如此让别人惊讶的干起了写小说这种事情……我选择了写作,仿佛一串佛珠,一颗一颗,轮回念动。我想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忘记,一边忘记的太多,一边还给我暧昧的希望。我想是蒙尘的记忆抛弃了我,内在的力量支配着我。我写下每一页文字,我故意忘记,换取更多力量接着写出一页,然后忘记。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