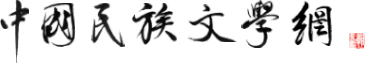一花一世界——《桑多镇故事集》之序言
刘大先
扎西才让的小说有一种空灵感,那种空灵感主要来自于冲淡的语言和迂徐的语调,并且他的大多数小说情节是去戏剧化的,那种去戏剧化也没有导向于日常性,而毋宁说它们普遍具有一种散文诗式的风格。事实上,扎西才让的写作最初主要的体裁确实是散文和诗歌,比如散文集《七扇门》和诗集《大夏河畔》。这几种文类在他那里彼此渗透,交互为用,除了外在形式上的些微差异之外,内在格调与风格上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这种风格的一致性,我认为来自于地方性——那种带有地域、宗教、族群文化色彩的表情达意方式、美学趣味和思维观念。
扎西才让的家乡具体来说是甘南,这是甘肃西南的一个藏族自治州,属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谈论扎西才让及其小说给我的印象,首先需要谈谈甘南给我的记忆和感觉。
2007年夏天,我从北京去西藏,经过甘肃,准备半道去甘肃佛学院找一位藏族学者同行,佛学院属于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就属于甘南。因为时间没有那么紧,我从兰州出发,乘坐长途大巴,先到永靖的刘家峡住了一晚,第二天去临夏转了一下河州老城,午后才出发去拉卜楞镇。沿途明显可见路边景物的变化,从童山濯濯、烈日炎炎,到逐渐出现零星的绿色——那是土豆秧和油菜,地势逐渐升高,路过一个叫做完尕滩的地方时忽然乌云密布,下起大雨来。车子慢慢吞吞地走着,傍晚到拉卜楞寺的时候天空居然放晴,风尘遍地,完全没有彤云密雨的迹象。
在夏河逗留了几天,去达宗湖,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走了许久,让人昏昏欲睡。可能是海拔已有3000多米,所以人容易犯困。终于到山顶,在一片柏树林中的空场地停了下来。白云在对面的山顶上幽静无比,林木苍翠,黄色的小花遍布在周围草地,是个人迹罕至的去处。不知道当初人们是怎么发现这里有个湖的,这是本地人所谓的“天湖”,也就是高山断崖湖。我下车提着祭祀用的米、风马、宝瓶往下走,湖水清澈湛蓝,静谧安详,只有少数几个游人。我在一个清烟缭绕的煨桑堆上放上新鲜的松树枝,看到有三个女喇嘛抬了个暗紫色的塑料桶,原来是放生。与陪同我的朋友顺着湖绕行了一周,柳树丛中有牛粪,散发出田野的气息。在树林中行走很不容易,时常会有枝条碰着脑袋,脚下的路也无所谓路,就是一些人绕湖踩出的痕迹,崎岖不平,潮湿的地方还有些滑。穿过树林,是个靠山的斜坡,更加难行,须要抓住树木的茎条才不至于跌倒。终于到达一处平坦的地方,修建了一处可供游人观览整个湖面的平台,从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扔“宝瓶”下去,有一大块地方的湖水已经被填满了。所谓“宝瓶”,是用白布缝制的里面装着青稞的口袋,每只袋子大约有半斤重,袋子缝得严严实实,并用印着花纹的黄、蓝、红色锦缎和金丝带缠裹起来。据说投掷宝瓶是为了祭祀湖神,以求神灵保佑,祈愿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入乡随俗,我抛撒了一些风马,也扔了一个宝瓶。
后来又去桑科草原,蓝天白云在强烈的日照下,空旷而又干净,没有什么特殊景色,但是草原主要就是一种氛围、一种气场、一种体验,至于草有多高、马有多肥、风有多大,都是次要的。朋友的一个亲戚是阿乃(尼姑),她的居所在寺庙隔壁的一个陋室,去的路上垃圾遍地,不时有浪荡的猪在四出拱泥土。房子是租当地居民的,狭小仄隘,除了一张床和一些炊具之外,别无长物。她殷勤地拿出馕,切西瓜给我们吃。我很不好意思,只是注意到她的年龄可能也不过30来岁,但眼角已有很深的鱼尾纹,可能跟此地强烈的阳光有关。关于她为什么出家,我没好意思问。
那是最初的甘南印象,当时还不认识扎西才让。但是读到《桑多镇故事集》里的篇章让我又回想起那些久远的经行碎片,它们自然而然,并没有焕发出异域风情或者别样的意态,那个大夏河边的小镇,小镇上的平常百姓,他们的寻常与传奇、艰辛与幸福都顺乎天然,也会经历现代性的冲击,但并没有撕心裂肺;也有尔汝恩怨,也不足以刻骨铭心。
2011年我去兰州参加西部文学论坛“文学甘南”学术研讨会,后来写了一篇随笔,谈到如果从学理上来说,当下的甘南具有的潜力足以使它成为西部少数民族和区域文学的生长点,所谓的“西部”其实是“地理发现”的产物,最初由西方的探险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活动与书写而诞生,如今这个“他者的发现”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因为本土作家的书写,甘南的表述成了“自我的发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甘南因为书写主体的变换,而迸发出不同的光彩。作为各民族文化交融并生的地方,这里的地方性智慧原本隐藏在地理的皮肤之下,如今走向小径丛生的路口。通过不同代际甘南作家的文本,可以看到原先伫立在我们脑海中那些有关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边地、中心与边缘、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一切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方式都失去了阐释的效力,我看到的只有混沌未分、相互关联的人、物色与情感风貌。
2016年5月末,跟随中国作家协会“重走长征路”的采访团,我又一次去到甘南。不过此次是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若尔盖草原,进入到迭部,走了碌曲、临潭等地。在郎木寺遇到了作为接待人员的扎西才让,在那之前我们可能在北京或者别的地方已经认识,但具体的情形已经记不清,似乎能记住的都与甘南有关系。两个月后,在以“诗歌视域中的地域性写作——甘南诗歌现象分析”为主题的“2016中国当代诗歌论坛”上我又遇到了扎西才让,不过这次他是以诗人的身份出席作为被研讨的对象。此后,我又去了尕海湖、玛曲草原和扎尕那。时隔10年,甘南自然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时间在这块空间中似乎变得缓慢,因而改变也从容而舒缓。我想这种时间感不仅仅是一个外来人的观察,可能也内化到扎西才让的写作之中,所以他的小说才会流淌着一种久违的古老诗意。
扎西才让早期的小说颇多摹仿流行的先锋小说之处,文本中不乏现代主义意味的疏离情感、冷漠态度、叙事圈套和结构技巧,然而晚近这些年他回归到了本土的叙事传统,即淡化描写和叙述,而着意讲述和抒情,让人与事自己呈现出冰冷或火热的温度。桑多镇是高原之中、草原之上、苍穹之下的一处平凡之地,这里发生的故事、经历的变迁、流露的情感和精神形态必然是地方性的,因为它们天然携带了由地理、文化、信仰所濡染的内质。但这种地方性不是孤立或排他的,它不拒绝变化也不刻意去变革,而是将外来的冲击与内部的蘖变都纳入到自发性的流动之中,因而很容易达到一种让他人可以理解与接受的效果。扎西才让的小说,如同这片高原上的野草边花,自足自在,纷纷开落,看上去是孤独的,却并不寂寞,因为它们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圆融的世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生命的郁郁勃动与天机的默默运行。
原文载于:《文艺报》2019年7月3日“少数民族文艺”版。
羊皮灯和桑多镇——《桑多镇故事集》之创作谈
扎西才让
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看顶棚上的羊皮吸顶灯。看得久了,视角会发生变化,仿佛自己浮于空中俯视此灯,进而生出许多想象来——
若这羊皮灯是座极有规模的建筑,那么生活在这巨大建筑里的人,就成就了一个故事丛生枯了又荣的家族。
若这羊皮灯是个小镇的规划图,那么这小镇就在藏地甘南,名叫桑多镇,生活在这小镇的人,虽身份、民族各异,但都叫桑多人。
很多时候,这个家族或者这个小镇,就悬在我头顶,发光,发热,甚至发出忙碌者无法听到的喧嚣声和呼救声。
这让我想起一部外国电影里的镜头:一头在森林里游荡的小象霍顿,突然发现:一粒飘浮在苜蓿花上的微尘,竟然是一座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无名镇。
这无名镇,在现实里,在我的笔下,就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中国小镇——桑多镇。平时,我就在其中生活,而在写作时,这镇子就被我用放大镜无限放大:我能清楚地看到谁在甜睡,谁在礼佛,谁在愉快地打电话,谁和谁在郑重其事地碰杯,谁和谁在口是心非地恋爱,谁和谁在争争吵吵中走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为了拯救那粒灰尘里的微小世界的居民,小象霍顿决定在所有动物的嘲笑声中顶着“幻想症患者”的恶名,将“无名镇”送回属于小镇居民的世界……而我,在写作之路上,也做出了和小象霍顿一样的选择:关注这个镇子上的居民,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尊重每一个人物的自由,珍惜每一个人物的生命。
甚至,我要借助于他们,唤醒这人世间被私欲遮蔽的温暖,呼吁世人继承善良、诚实、仁慈的美好品德,恪守自省精神,滋养悲悯情怀,共建和谐社会。
现在,《桑多镇故事集》 将与读者见面,这里头收集的13篇小说,也仅仅是桑多镇——这微小世界里发生的有点意思也有点感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然只是诸多桑多镇故事中的一鳞半爪,我试图用笨拙的声音讲述出来,哪怕讲述得不是太到位,不是太有趣,我自己觉得,这对这个藏地小镇而言,对一个边地写作者而言,也是有点意义的。
这本书,或许就是此刻悬在我头顶的羊皮灯,发着它的光,发着它的热,它里头的小人物,也在发出只有小象霍顿那样的读者才能听到的几不可闻的喧嚣声、呼救声和祈祷声。
而这本书,也仅仅是桑多镇故事的开始。
原文载于:《文艺报》2019年7月3日“少数民族文艺”版。
作者简介: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学、近现代文学和影视文化的相关研究和评论,出版《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无情世界的感情》等多部专著,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年度评论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等奖项。
作者简介:扎西才让,藏族,1972年生,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诗歌八骏”之一。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诗收获》等转载并入选多部年度作品选本。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海子诗歌奖、三毛散文奖、梁斌小说奖等文学奖项,荣膺第四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著有诗集《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中短篇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入选201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